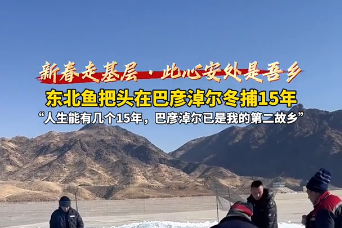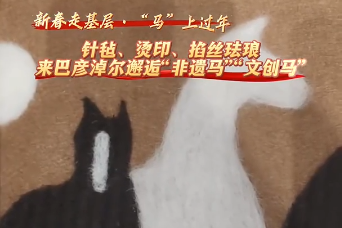每当黄河来水量陡然增大时,洪水就会漫过渠堤,淹没大块良田沃土,形成洪涝灾害;每当黄河来水量突然减少时,许多渠道又难以进水,造成大面积土地干旱歉收或绝收。当时有民谚:“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
二是,很多渠口水位不够高,引来水后,海拔高于渠口的耕地却无法浇灌。同时,几大干渠相互影响,致使下游渠道进水不易。上游渠道水多淹地,而各大干渠都没有退水渠,用不完的水排入阴山脚下的滩地、洼地,淹没了牧场、道路和部分农田,农牧业生产都深受其害。
三是,黄河冲淤淘凌严重,八大干渠的引水口常常淤积报废,河套地区年年需要组织大批强壮劳力在开春时节去捞挖还处于冰冻状态中的各渠道引水口。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挖掘机械设备,人们光腿站在漂着冰凌的河水中作业。土方量动辄数百万立方米,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因此患病致残。每年捞挖渠口成为河套人民的巨大负担。
1920年,河套干渠被军阀杨以来强行征收管理。军阀爪牙既无水利常识,又唯利是图,不管民生疾苦,不顾整理渠道,使各渠道淤塞失灌,河套之田日渐荒芜。
开挖了八大干渠的治水天才王同春,一生都想实现“一首制”的蓝图,却终未成功,抱憾而终。
1932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今北京交通大学)的王文景受聘于阎锡山屯垦队,成为河套水利建设的一名技师。
科班出身的王文景眼光独到,甫到河套灌区,就敏锐地发现多个口子从黄河直接引水的弊端:没有引水闸,极容易因引水失控造成灾害,但若要建造坚固的引水闸,又会因黄河河道摆动不定而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这个难题困扰了王文景很久。直到一天,他看到当地群众就地取材用土生土长的红柳、河柳、枳芨、哈木儿以及麦柴这些做成“叠埽棒”来打坝,于是灵机一动,决定用这个土办法来做草闸,既坚固又省钱。
当年,第一座草闸在永济渠二喜渡口处建了起来。草闸强大的控制水量和分水调水的功能解决了河套灌区一大难题,在当时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受命驻守河套。1940年2月,日军从安北、五原、临河一直打到陕坝,而傅作义节节后退,等待反攻时机。3月20日,黄河解冻,各大干渠水流滔滔,傅作义决堤放水,河套大地一片汪洋,日军寸步难行,傅作义取得了著名的“五原大捷”。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河套灌区和河套的农民作出了巨大牺牲。傅作义决心重建河套灌区的水利设施,以报答这里的父老乡亲。
1941年,傅作义委王文景以重任,要求他整顿和恢复河套灌区的农田水利设施。王文景十分振奋,组建了绥西水利局,又组建了河套六县水利局和黄济、永济两大干渠管理局,开挖复兴渠、修建黄杨接口、整修乌拉河、整修杨家河……河套灌区的水利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河套灌区多年治水的过程中,王文景深切地体会到多个口子直接从黄河引水不仅给百姓带来灾难,还严重制约着河套地区农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的王文景经过认真思索,制定了《绥远省后套灌区初步整理工程计划概要》,大胆地提出了“一首制”的想法。
王文景认为,河套灌区的诸多问题,非“一首制”不能解决。他提出,在磴口县二十里柳子处修建“一首制”拦河坝,有控制地引水,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同时将后套及三湖河灌区合并整理,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可惜,由于工程的投资规模过于庞大,国民政府无力承担,所以“一首制”方案只是存在于人们的理论探讨层面。
“一首制”有点遥远,王文景退而求其次,又提出了“四首制”的方案,计划将十多条干渠设置在黄河上的简易土堆引水口合并整理成四个永固石闸引水口,以便很好地解决灌区的防洪防涝问题,减轻河套人民每年捞挖渠口的巨大负担。1947年,绥远省政府组织人马开始修建“四首制”中的第一首——黄杨闸永固石闸,但后来还是因为工程款不济,只是在黄济渠与杨家河两渠口附近开挖了两个闸基坑后便终止了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