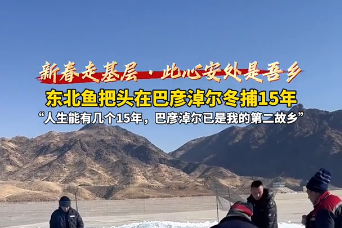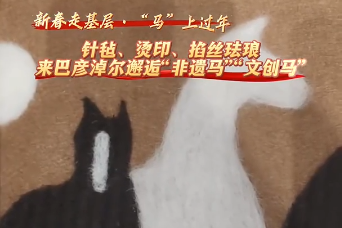碾磨前老骡子的蹄音里、村道上二饼牛车的辙痕里、院角包浆的农具里,都嵌着春种秋收的故事。
那些凝固着黄土地上千百年来佝腰扶犁剪影的农具、农事,将消逝的农耕记忆酿成醇厚绵长的乡愁。
——编者
农具的变迁
□吕成玉(临河)
正月初三,我们回到家乡看望耄耋之年的大哥大嫂,大哥家前几年盖的新房仍以鹤立鸡群的姿态矗立于村子中央。宽敞四围的院落方方正正,窗明几净的住房洋溢着欢度春节的喜庆与温馨。玉米棒小山似的堆积在院子中央,在春阳的映照下泛着金黄色的光芒(我估摸是去年秋天玉米价格过低,侄儿才放到现在待价而沽),特别是东西两侧布局有序的农机具房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喝了几口茶后便来到院子中。

和侄儿交谈证实了我的想法,侄儿说去年玉米由于价格偏低未卖,农产品价格不稳种植难以把握。而后我依次查看了他们的农机具:西面的车棚内停放着四轮车、电动小三轮,以及耘锄机;东面的车棚内停放着十几台播种机和旋耕机。我算了算,除了没有收割机和脱粒机,春种秋收的农机具基本齐全。我问侄儿一台播种机多少钱?答曰:两千多元,用四轮车牵引日播四十至五十亩,也属于大型农机。现在生产的是二十四腿播种机,播种更快;一台耘锄机日锄地十多亩,主要用于玉米葵花地的松土除草;旋耕机用于平整土地;那辆前几年买的四轮车则花了四万多元。我说:地里的收入全靠这些农机具了。侄儿笑着说:不购置不行,这些农机具现在家家都有。
现代化的农机具凸显出强大的优势,就播种而言,过去全靠人力。比如种小麦,一人牵马帮耧确定前行的方向,在人牵马走的过程中将籽种播入土壤。但毕竟是人工操作,麦垄或宽或窄、籽种或稠或稀,很难做到行距和籽种均匀,所有瑕疵在麦苗出土后一目了然。加之管理粗放,一亩粮田便有了牛吃心马吃畔的折扣,也就有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窘迫。
唐代元稹在《田野狐兔行》中写道种豆耘锄,种禾沟甽。耘锄在古代就是一种松土和除草用的锄头。过去播种玉米全靠人力畜力,玉米出苗后必须人工间苗,需要大量的劳力,一个成年男子起早贪黑一天可以锄地间苗一亩半左右。而现在的耘锄机每小时轻松锄地二亩至四亩,省时省力。现在耕地采用深耕旋耕的方式,播种使用的是精密播种机,可以随时调整播种量和苗间距离。去年侄儿种植的26亩玉米,利用机播一上午就种好了。
记得小时候老家院子西侧有一间小土屋,既是存放粮食的凉房,也是堆放农具的杂物间。那时的农户都有镰刀、锄头、铁锹、铁铲、扁担和箩筐等几件简单的农具,犁、耧、牲畜、大小胶车等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碾小麦主要靠牲畜拉着碌碡进行,我朋友回忆他那时碾场的经历:炎炎烈日下其他社员都回去吃午饭了,他独自驾驭着两个双马碌碡、三个单马碌碡碾场。汗水浸透了衣服、脚也烫得发疼、嘴里像着了火,依旧丝毫不敢懈怠。因为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马和碌碡碰撞的严重后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哥家分到了一辆驴车,农户们的生产工具也在不断更新。有的用积累的资金购买了牲畜、买了木耧,有的购买了四轮车等农用机械。以四轮车为例,它确实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好多问题,既可以带着碌碡耙地、碾场,又能运输农作物。这些先进生产工具的添置和更新,彻底将农人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头顶烈日汗洗脸的繁重劳作中解放出来。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从小生活在农村,耳濡目染中我也学会了使用农具。十五六岁时,每到暑假正逢龙口夺食的紧要关头,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夏收。那把弯弯的镰刀曾多次割破我的手指,但每次总是简单包扎一下就继续抢收,反复地挥镰弯腰让我从最初的笨手笨脚逐渐变得动作协调。听着镰刀落在秸秆上的沙沙声,看着身后一铺一铺的麦秸,太阳的炙烤、麦芒的刺痛、汗水的蛰眼、衣衫的浸透、浑身的疼痛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也曾随母亲在自留地畔点瓜种豆,蹲在集体农田为玉米除草间苗。更多的时候,放学后和几个发小挎着箩筐,拿着小铁铲到田埂地畔掏苦菜用来喂猪,以期家中的猪尽快长大长肥。当苦菜装满了箩筐后,我们会仰面躺在田埂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和游弋的白云。耳边传来云雀的叫声和昆虫的低吟,鼻间充盈着庄稼的清香,整个身心融入大自然,感受着少年时代的自由与美好。参加教育工作后,我曾多次带领学生在课余时间帮助生产队锄小麦、掰玉米,挑着扁担箩筐参加农田大会战和疏通总排干,涔涔汗水挥洒在广袤的土地上,心中孕育着五谷丰登的希望。成家后由于妻儿是农村户口,我便有了亦农亦教的身份,有了三亩麦田一抹夕阳的诗情画意;也有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劳与乐趣。
跳出回忆我看到车棚的墙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镰刀,便问侄儿这镰刀现在还用吗?侄儿说偶尔也用一下,夏天和秋天到地堰上给羊割些草换换口味。咩咩的叫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我们走向羊圈,十几只大绵羊正在晒着太阳,看到我和侄儿到来纷纷站了起来,伸着脑袋望着我们。
农具的变迁,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轨迹。点灯不用油的目标早已实现,耕地不用牛的期盼如今也变成现实。各种收割机、脱粒机、喷药机、小麦灌溉喷水机已遍布农村,成为广大农民得心应手的现代化农业工具。赋闲的农具静静地躺在农家的院舍或农耕博物馆,回忆着流逝的岁月、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美好,也将一缕缕乡愁印在黄土地上,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推碾拉磨的老骡子
□王有义(临河)
河套农村有一句俗话:“推碾拉磨的老骡子,精打细算的老婆子。”意思是:要用碾子把糜子、黍子、谷子等推成米;用磨把小麦、豆子、玉米等磨成面,最好使唤的是老骡子。论会过日子,能勤俭持家料理好家务,当然是上了年岁的老婆子了。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村子里没有米面加工厂,米和面都要到碾房磨房去加工,推碾围磨就成为农民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了。要是一个生产队有一匹推碾拉磨好使唤的骡子,确实是一件值得社员们庆幸的事情。因为骡子有马和驴杂交的优势,所以它的使役价值要比马和驴高得多。骡子体质结实、生命力强、抗病性好、耐力强、饲草料利用率高,又便于饲养。马生的骡子叫马骡,毛驴生的骡子叫驴骡,我们队就有一匹马骡,几乎一年四季都用来推碾拉磨,让人们使唤出了灵性。
这匹骡子是1957年农村合作化成立高级社时一户农民入社的牲畜,当时是一匹刚满两岁已经阉割了的马骡条子,十分招人喜欢。它体格矫健、腰身修长、棕色的皮毛又光亮又顺滑,用手触摸像绸缎一样,耳朵立格楞楞的、眼睛圆滴溜溜的、尾巴紧密生生的,最让人喜欢的是四只蹄腕部位都长着洁白的蹄毛。因此,有了一个一生未变而且十分好听的名字“四银蹄”骡子。四银蹄在一些驾驭牲畜高手的调教下,对推碾拉磨这种活计上了道越使唤越顺手,不知不觉承担起村子里推碾拉磨的任务。有的人家为了能够使唤上四银蹄,需要提前几天和饲养员打招呼。
四银蹄是一个乖顺听话有灵性的牲畜,不论男女老少,只要饲养员从槽头上把四银蹄缰绳解开递到手里,它就会很顺从地让人牵着走,不甩缰、不后退、不撒欢。到了碾房磨房,只要人拿起套缨,它就会主动地把头伸过来,让人从容不迫地给它戴在脖子上。它还会站到磨道一个十分合适的地方,让人给套上夹股、拉绳,蒙上眯眼布。只要人轻轻喝喊一声,四银蹄就会迈开节奏均匀的步伐,行走在磨道里。但是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吴二楞。当时二楞是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正是顽皮捣蛋的时候。他拿着一个鞭炮,故意在四银蹄耳朵跟前点着,一声爆响,吓得四银蹄挣脱缰绳,冲出饲养院大门跑到很远的地方。饲养员刘大叔端着豆料笸箩,呼唤着四银蹄,费了很大的劲才哄回来。从此四银蹄一见二楞便又踢又叫又咬,二楞再也不敢使唤四银蹄了。
四银蹄通人性,它在拉磨的时候能够听出石磨旋转的各种声音。磨斗里如果没有粮食了,上下磨盘就会发出一种空洞的隆隆声。有时候围磨的人没有发现,四银蹄也会乖乖地停下来,绝不会拉着空磨旋转,因为转空磨是很伤磨齿的,还容易把小石子掺和到粮食里面。磨房里一般都会配备一张脚蹬的大面箩。面箩用绳索悬吊在长方形的面池上方,围磨的人把磨台上磨下的麦碴用笤帚扫到簸箕里倒入面箩,用双脚来回蹬踏箩杆下面的一个装置,面箩里的麦碴就会均匀地在箩底上滑动,面粉纷纷落入面池。拉磨的四银蹄能听得懂蹬踏面箩的节奏,每到一箩面刚好箩净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让围磨人清扫磨台上的麦碴、往磨斗里加入新的磨料、调整磨眼里的搅料棍子。等把这些程序都干完了,它又迈开拉磨的步伐。
人们说四银蹄是个牲畜里的君子。围过磨的人都知道,有很多拉磨的牲畜会趁人不注意偷吃磨台上的粮食,接着便会遭到呵斥鞭打。为了防止牲畜偷吃,要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撑竿,一头绑在拉磨牲畜的笼头上,一头拴在磨盘的一个橛子上,牲畜就没办法把嘴伸到磨台上了。四银蹄不会受到这种严苛的管制,因为它从来都不会偷吃一口磨台上的东西。即便磨豆子面的时候,磨房里充满豆香,对一个牲畜来说,这是极大的诱惑。四银蹄却不为所动,充其量在这种香味的熏陶下,连续打几个响鼻。这让人们感到:四银蹄好像还懂得一点儿道理,能管住自己、不放纵自己,反而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体面,也能免受一些皮肉之苦。人们还说四银蹄在拉磨之前,都要在外面撒尿屙粪,只要一进碾房磨房就再不屙尿了,直到卸套休息。不像别的牲畜,推碾拉磨期间,想什么时候屙粪就屙粪,想什么时候撒尿就撒尿,搞得人们手忙脚乱,又扫粪又垫土,碾磨房里总是臭烘烘的。还有一件更让人惊奇的事情在村子里被人们常常说起。有一个社员半晌午套着四银蹄围磨,磨房门开着,不知道什么时候邻居家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悄悄溜进了磨房。围磨的人正在聚精会神地踏箩响声很大,没听见也没看见进来的这个小孩。小孩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挪着小脚走到磨道中间。四银蹄戴着眯眼布,肯定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不知道是它听到小孩走步微弱的声音,还是嗅到了小孩身上的气息,还是有一种特殊的心灵感应,四银蹄乖乖地停在小孩面前。围磨的人意识到四银蹄不走了,还大声喊了一声:呔!四银蹄仍然一动不动。围磨的人起身看了一眼磨道,眼前的一幕吓得他几乎瘫坐在地上,小孩正伸出小手摸四银蹄的腿,四银蹄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祸。围磨的人赶紧把小孩抱在怀里走出磨房。邻居家的人正在院子里找小孩,围磨的人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邻居连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骡子是个转世的菩萨”。
197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传来一个很让人揪心的消息:四银蹄跌倒在磨道里站不起来了。队长立即派人到公社兽医站请来兽医,经过详细检查后兽医说:这个骡子不是病倒了,实在是年岁太大了,把全身的力气耗尽了,就像一个百岁老人,油尽灯枯再也站不起来了。人们把四银蹄抬到小胶车上,拉到饲养院外面的转槽旁。闻讯来了很多人,有抱着小孩的妇女、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一个社员凑到队长跟前说:老骡子反正站不起来了,不如趁现在还活着,杀了它大家分些肉吃算了。一些社员听到这句话觉得很不是滋味,饲养员刘大叔说:这话说得也太没有良心了,老骡子在生产队推碾拉磨几十年,几代人都使唤过它,碾过的米、磨过的面,堆起来有座山了,这是咱们队的功臣啊。你们就是杀了它,我也不吃它的肉,我怕造孽。一个妇女蹲下来,用手抚摸着四银蹄的耳朵、脸颊、鬃毛、身子,直至尾巴。眼泪汪汪地对队长说就让它静静地躺在这里吧,饲养院就是它的家,它也该休息了。中午时分,四银蹄呼出最后一口气闭上了眼睛。队长让几个饲养员在西渠边挖了个坑把四银蹄埋了,不知道是哪个社员还在旁边栽了一溜榆树。
40多年过去了,包产到户之后饲养院所占的地方被开发成耕地了,找不到一点过去的痕迹。曾经使唤过四银蹄推碾围磨的人也不多了,四银蹄的故事也很少有人再提起,由于农田规划,原来的西渠也改道了。可是村子里的人直到现在还把埋四银蹄的地方叫骡子圪梁,那一溜榆树也还在,春天榆钱挂满枝头、夏秋绿影婆娑、冬季枝条在寒风中摇曳,几只喜鹊在树上跳跃。看到这般情景我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万物皆有灵,天地共生荣;善念爱无痕,尘世总光明。让我们善待每一个生命吧,哪怕是一株小草、一只蝼蚁,甚至是一缕清风。
二饼子牛车
□白秀英(五原)
二饼子牛车拉白菜,小妹妹坐在车辕外。河套的深秋金风送爽,一辆牛车悠闲自在地行驶在乡间小路,车上装满了翠绿的白菜。一对青年男女柔情似水,含情脉脉地分坐在车辕两侧,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田园秋景图啊!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河套农村的乡间小路上,时不时会有一辆辆牛车走过,农村人又叫它二饼子牛车。它的全身都是用木头做成,两个一米高的车轮用厚厚的榆木板拼成,像两张巨大的面饼,因此人们叫它二饼子车。它的车轱辘和轴固定在一起,行走时一起转动。车身和车辕是柳木做的,杏木制成的车轴为了耐磨镶着铁车键,车键处经常涂抹些植物油起到润滑作用,因此牛车上配有装油的油葫芦。由于车轴经常上油,所以黑乎乎的,那时候孩子们不太讲究个人卫生,所以常用脖子脏的像车轴来形容。
乡村的土路不平坦,二饼子牛车走起来很笨重,再加上没有轴承,走起来吱吱扭扭响个不停。人坐在车上摇摇晃晃、上下颠簸,有种醉酒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也喜欢看车辙,车轮碾过尘土飞扬,两条永不相交的车辙框住车道中间的牛蹄印,无规则地在大地上画着素描。
在现代人的眼里,牛车很不起眼,但是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牛车是农民们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小时候常听祖父讲起,他就是赶着一辆二饼子车,从陕西府谷县老家走西口来到河套的。过去的陕西府谷县,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遇上灾年粮食颗粒无收,很多人都没有饭吃。他听人说河套是个吃白面烧红柳的好地方,于是他带着妻儿老小,赶着一辆笨重的二饼子牛车,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月,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终于来到了河套。从此过上了吃饱饭的日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清末民初,有很多移民都是赶着牛车来到河套地区的。所以对于河套人来说二饼子牛车是神圣的,为远离贫穷与饥饿,它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由数辆牛车组成了村里的运输队。供销社分配化肥了,牛车到供销社拉回化肥;秋天丰收了,队里的几辆牛车又装上粮食,一车车往粮站送去;村里要放电影了,牛车把放映机拉回来;春播时,十几辆牛车往地里送粪肥,牛拉着几百斤重的粪肥喘着粗气,牛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犹如一首悦耳的乐曲,给忙碌的田野带来了乐趣。
春夏之交,生产队里种的韭菜、小白菜、水萝卜等蔬菜长大了,队长带人收割了菜,让父亲和同村的赵大叔两人各赶一辆牛车去县城卖菜。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就吵着要跟父亲他们去县城里,父亲拗不过就同意了。天还没亮,两辆牛车就满载着新鲜的蔬菜出发了,薄雾蒙蒙、晨风习习还有些凉意,不过走起路来就不觉得凉了。我走了一段路就觉得有些疲惫打起了瞌睡。这时赵大叔突然放开喉咙,唱起了爬山调:二饼子牛车拉沙蒿,它是我家的传家宝。二饼子牛车车辕长,牛车拉菜比人强……歌声和牛车咯吱咯吱的声音飘荡在空旷的乡野上空,顷刻间大家都提起了精神来。当太阳升起时,我们已经到了菜市场。吃完两毛钱一碗的绿豆凉粉,父亲和赵大叔把牛拴在外面空地的一棵树下守着菜车卖菜,让我别走动,等卖完菜再逛街。父亲经常赶着牛车去县城卖菜,不仅会给我们兄弟姐妹买回一些糖果、麻花、糖麻叶之类的零食,还喜欢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在县城听到的新鲜有趣的故事和一些卖菜的经历。
随着时代的进步,生产队里有了马拉的大胶车、毛驴拉的小胶车,牛车逐渐被淘汰。如今各种现代化农用机械承担起耕种、运输等任务,二饼子牛车也已静静地躺在了农耕文化博物馆里,它真实地记录着半个多世纪农村的交通运输,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也承载了几代人的生活梦想。如今开着汽车行驶在城市道路上,看到的是繁华中的拥挤。途经乡间小路,美丽的景色一晃而过,也没有了牛车上那种浪漫的情怀。我把牛车当作生命里的一份回忆写成文字,希望人们了解刻满岁月痕迹的二饼子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