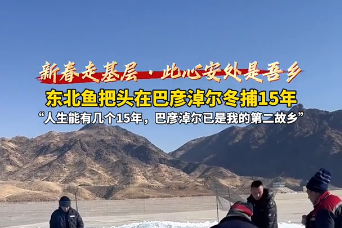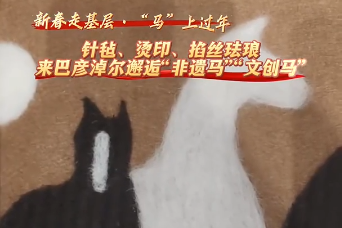在阴山南麓、黄河北岸的辽阔大地上,坐落着一个叫阿吉奈的小镇,乌纳嘎图河从小镇中间南北向蜿蜒而过,一座吱嘎作响的小木桥横跨其上,不仅连接了河的东西两岸,也连接了六个小女孩用童真结下的纯洁友情。她们常常在小木桥处相聚,共度打沙枣、挖野菜、拔苦豆、拾煤渣的欢乐时光。高莉芹入选内蒙古出版集团精品图书展的长篇小说《风挡》就是在这片宁静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缓缓铺开了六个女孩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
故事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以承英——六姐妹中的佼佼者为主角,十七岁代替哥哥到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人生旅程。从当拖拉机手、和天津知青的失败婚姻到跑长途货运等一系列跌跌撞撞、或惊险或无助的人生际遇,让读者随着她命运河流的激荡起伏同悲同喜,在感受现实惊涛骇浪的同时,也看到了闪耀着人性的温暖波光。
一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灵魂,如何塑造,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和价值。很显然,在《风挡》这部长篇小说里,高莉芹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精雕细琢,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品开篇“打沙枣”开门见山把主人公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承英像猴子一样爬上树,坐在高高的树杈上,脖子上挂着的书包随意耷拉下来,好像袋鼠肚皮上的小口袋。她用手拽过一根沙枣树枝,捋下一把沙枣,装进书包。”这是我们熟悉的乡村孩子打沙枣场面,其他小姐妹在树下捡沙枣,站在树上打沙枣的唯有承英,主人公大胆、泼辣、假小子般的性格跃然纸上。
作者匠心独运之处就在于她的人物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注重了形象的个性刻画,还重视了形象立起来的基础,也就是主人公成长环境的呈现。承英的父亲背驼,母亲腿瘸,虽然他们靠擀毡和裁缝技能把日子过得比小镇的其他居民殷实一些,但被歧视和嫉妒仍然让他们摆脱不了做人的卑微状态。生长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加之既不是长女又不是独生女,承英成长得非常皮实,独立性强,还敢于抗争。当了知青的承英成为了拖拉机手,为了干活利索,她脚上穿一双球鞋,裤脚挽起来,一头秀发扣在帽子里,打扮更加男性化,为其后续的形象发展奠定了基调,也埋下了伏笔。结婚后,承英与天津的婆家从穿着习惯到生活方式都大不相同,注定了她很难融入其间,最终婚姻破裂。年轻时不愿外露、被忽视的一头秀发和中年时历经生活磨难、无暇打理的一头凌乱短发形成了鲜明对比,“如荒草般竖起来”的短发扎痛了读者的心,也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主人公生活的沧桑变迁。
作品的神来之笔是抽烟这一细节的描写。承英插队后,离开了家的束缚,个性发展更加凸显,其中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学会了抽烟。从当初的好奇尝试到最后成为她生活压力的舒缓方式,“‘就靠这口烟活着,还戒它干啥。’承英那一堆的烦心事,就依靠这口烟为她排遣,也不知是没办法戒掉还是不想戒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作品中多次出现承英被生活逼到绝境时,下意识地掏出烟,猛抽两口,吐出不同形状的烟圈,接着是剧烈的咳嗽。直至送儿子到自治区重点中学上学,顺便在发小的医院检查出肺发黑,读者对重压下的承英产生了隐隐的担心。出轨的丈夫被公安带走后,“承英坐在炕沿上,哆哆嗦嗦地摸出一支烟,那动作像极了年迈的老人……她从衣兜里摸出打火机,可手抖得火苗左右摇晃,好不容易才点着,一口烟从嘴里喷出来,咳嗽声随之而来。她佝偻起腰,缩成一个小人。”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抽烟并不能帮助她化解压力源,只能成为她在重压下快速衰老的强烈烘托。
《风挡》在人物群像的刻画上也很成功。如在夹缝中生存、精明干练的母亲,满身书卷气的杏子,胆怯的春雨,大大咧咧的门墩等,都给人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
二
讲好一个故事对一部小说至关重要。《风挡》的叙事节奏简洁明快,毫无拖沓冗繁之感,但故事却是跌宕起伏,层层递进,引人入胜。承英婚姻失败后从天津回到家乡,进入物资部门工作,失业后,命运把她推向了跑大车运输的道路。再婚嫁给了和自己合伙跑大车的孙果山,自己生活艰辛,还要照顾因童年创伤精神受损的妹妹、重病的姐姐、上学的儿子……生活中的矛盾、问题都要由她来解决,而她自己身患重病却要独自扛。“我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要强,要么要饭,我只能选择要强。”就是这个信念让承英一直坚强地走下来。但丈夫的重病住院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忽然觉得好累好累,闭上眼睛睡着了”,即使醒来后,“她的眼睛好像不听使唤,就想闭着。她多么希望眼睛永远就这样闭着,不用看这乱糟糟的现实,不用听让她崩溃的消息,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着。”这是故事发展的高潮部分,主人公承英完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直看她坚强的读者终于看到了她柔弱的一面。作者只有走入人物的内心深处,才能写出这样直击心底的动人情节。
因自己读书不多,和小姐妹们拉开了人生的差距,承英决心把儿子培养成功,弥补自己的缺憾。在儿子从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并被北师大录用后,她满心欢喜,挨家给闺蜜们报喜,展示了她性格可爱的另一面,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一部作品中,一个好的名称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不得不说,作者用“风挡”作为整部作品的主题意向颇为生动贴切,寓意深远。作品中,承英对汽车风挡玻璃非常珍视,经常擦得通体透亮。在青海,一次驾驶过程中,汽车风挡玻璃被飞溅物砸了一个不小的窟窿,对行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承英心想,风挡玻璃是车辆的保护屏,风挡一旦漏风,车就得停下;自己也一样,现在还不能倒下,一定要撑下去,为这个家遮风挡雨。”作者用具象的故事情节把“风挡”的寓意完美地体现出来。儿子铁蛋的感受为这一意向作了更好的诠释:“铁蛋觉得母亲在他前面,就像大货车上的风挡玻璃一样,能为他遮风挡雨,不论遇到什么风云突变,他都不会惊慌失措。可母亲内心的风雨来了后,谁能为她遮挡呢?想到这里,铁蛋咬咬牙,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口气,将来成为母亲生活中的风挡。”“风挡”的意象在故事中经历三重嬗变:初为遮护肉身的玻璃屏障,继而化作精神穹顶的透明盔甲,最终在铁蛋的凝视中升华为代际传承的能量场。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一条河流相伴,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一座桥的支撑。”乌纳嘎图河不仅流淌在阿吉奈镇,它还流淌在整部作品里,流淌在每个人物的血液里。读书最多的杏子成年后回到河边,才明白“这条河早已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了,这流动的水就像身体里的血液,和自己融为一体”。饱经风霜的承英走在乌纳嘎图河的桥上,“看到桥下的树干布满风蚀斑驳的痕迹,那一道道纹理就是年轮的记忆,有多少时光在河水的流淌中消逝了,那些儿时的玩伴各奔东西,只有两岸的垂柳,每到夏季,不褪永恒的绿,撑起小镇旖旎的风光。”一条小河有流不尽的乡愁,一座小桥是对故乡的守望,它们凝聚了作者无尽的情感,让作品更加唯美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