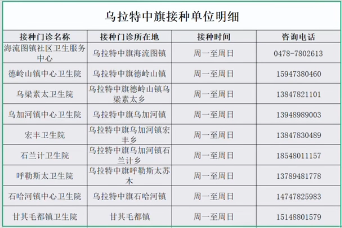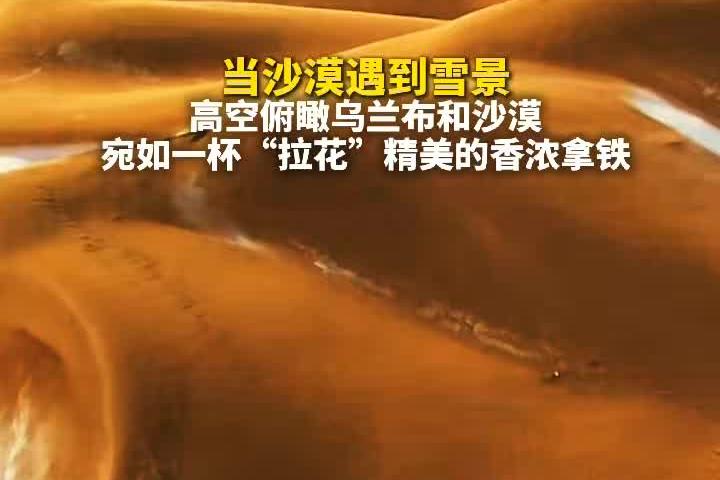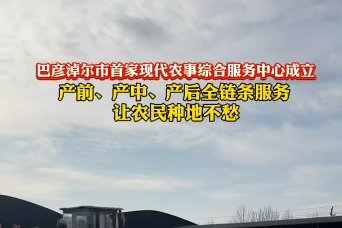吃了豹子胆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六个月。在乌兰布和沙漠生活,哪个人的胃里没有二两沙?谢鹤仁就是以这样幽默风趣、生动形象的语言,写出一部十七万字的纪实生态文学作品《渐渐消失的沙漠》。该书讲述的是,他的父亲、“大漠愚公”——谢恭德,带领全家人治沙的故事。
《渐渐消失的沙漠》第一章节基本是纪实,把乌兰布和沙漠及磴口县的地理概况、来龙去脉,人口分布、生存现状等介绍得详详细细。而这不过是虚掩门缝,旁观侧立。从第二章节“家庭会”开始,谢鹤仁作为一个诗人的语言天赋显露出来了。
“大地像母亲的子宫,孕育出五谷,孕育出山川河流,也孕育出生老病死”“祝福的言语软绵绵的像一团毛线,再不像进树林放羊时的口气,一出口就横刀立马”……这些句子,似机缘巧合,欣然来到他笔下。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肚子吃饱了,随便在沙窝躺下展展腰,什么蓝天白云,什么理想人生,在这个时候都是浮云,我们的眼皮比锹头还重。”为了挖渠,父亲卖了一头猪,那是老农民一家人一年的油水;甚至背着老伴儿,把给大儿子娶媳妇儿的钱拿出来花了。“当时大哥二十五岁,我二十二岁,三弟二十岁。一家三个光棍儿子晃来晃去……”要是一个平庸的作者,接下来肯定会用大量篇幅去写父亲为治沙,是如何苦口婆心做母亲的工作,谢鹤仁没有,直接在第二段手腕一抖,写道:“他眉不秃,眼不瞎,找不到媳妇能怨我?”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在外人面前,父亲是最讲道理的人。他在外头讲大道理,回到家讲小道理。
接下来一句:我们是父亲的三套马车。“五把锹并在一起,就是推土机”,把情节拉满,让读者的心紧绷起来。
谢鹤仁特别擅长对日常生活、劳动细节的描写和对人物内心思想斗争的捕捉,那自然是因为他太熟悉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说起他的苦豆坑,西沙窝、白茨圪蛋、开渠、栽树、种草、担土、甩锹,如数家珍。他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凭着“看沙子厉害,还是我厉害”的一股狠劲儿,“风啃不动石头,父亲就用石头挡树苗;石头没有了,父亲就捡起渠里挖出的红土结成的坷垃挡树苗;坷垃用完了,父亲就找酒瓶、穿破的鞋、穿烂的衣服、锄和锹等,只要能挡风沙什么东西都行。实在找不出快速压沙的宝贝,父亲就担红土来压”。从一开始的沙漠里种树,到最后树地里套沙,谢鹤仁没有故意拔高父亲的形象,只是将他日常的点点滴滴真实记录下来,不含“水分”。
纪实文学,既然称之为文学,就一定需要作家的艺术创造,结构的安排,人物性格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形成、化解等等。既不能违背自然写实的状态,“破坏生态”,也不能主观过强,用心过切,否则就成了“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一字不落地把过去发生的事儿如实记录下来,就又成了流水账,只能算是一种文字性资料,不能称其为文学作品。
苦难的名字是生活给的,就像乌兰布和的名字是风给的。栽树就得浇水。在高五米、宽五十米开外的沙漠中挖渠,可想而知。他写道:第一天,欢声笑语;第二天,少言寡语;第三天,不言不语。
“母亲看我们累成这样,为了节省体力,就把锅背进沙漠里做饭。我们在地上掏个窑,把锅放上去就是炉灶。沙蒿和白茨不缺,柴到处都是。面是母亲在家揉好的。由于没有烟囱,在揪面的时候,面被烟熏了,煮熟后发苦。这倒没什么,饥不择食嘛!吃完面,碗底会有一层沙。父亲说,在沙漠里居住的人不吃三斗沙土不叫大漠人。”母亲走后,他在纸上“讨伐”完父亲,又原谅了父亲。“我想,什么是根,根就是祖坟,父母去世后埋在哪里,我们的根就在哪里。”
本书在适当的场合加入了作者的一些诗作,起到烘托效果的同时,也让读者有了意外的收获。那些诗作铿锵有力,轻则取人泪水,重则动人魂魄。书中还运用了大量生活化的语言,比如“钱是硬头活气”“年年盼着年年富,年年穿着叉叉裤”等。其中有一句,我想大部分读者未必会在意,即“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保护神”。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在乌兰布和,梭梭就成了沙漠的保护神。然而,我却不愿这么轻轻地将它放过。以我对谢鹤仁的了解,这恰恰体现出他是一个内心有坚守、有信仰的人。
“我们偶尔也会喝酒,喝过酒的空瓶子在房后横躺竖卧着。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要是把酒瓶里灌满水,插进树苗,然后挖个深坑埋进土里,不知会怎么样?……树就活了,我把它称为‘酒瓶里的春天’。”
他活成了一棵树。
一位作家说: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自己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谢鹤仁的喉咙已经打开了,就待字正腔圆地唱下去。一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当你顺其自然时,磨不推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