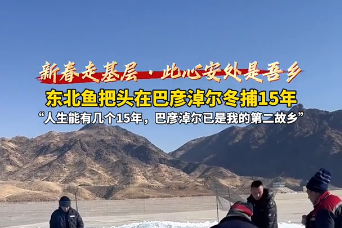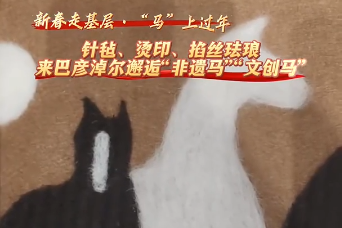五岁学诗,先生是父亲。一次中饭,父亲用筷子指我,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先是一怔,随即忙把桌上的饭粒舔食干净。父亲笑了,以为我听懂了他的话。又说:“跟我读!”随后,他一句,我跟着读一句。两遍过后,命我:“背会了,明天考试。”我心不在诗,在我碗里的饭、盘里的菜,更不知“考试”为何事。次日午饭时,父亲说:“背来听听。”见我一愣,他瞪眼看我,我霍地想起他的五字一串的话,忙说:“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单打……”不等背完,就听得“啪”的一声,脑袋瓜儿挨了一巴掌。疼不怎么疼,声音着实响。见一家人“哈哈”笑我,我“哇”地一声,扑进母亲怀里。
父亲读过私塾,字写得好。他读过的诗也多,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五言七律,都是名家诗句。
父亲笃信“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继承了私塾先生的衣钵,修一块板子挂在墙上。听说两个哥哥尝过那板子的滋味。我厌恶他的板子,却又知父命不可违,所以背了许多诗,都也似懂非懂。
后来知了些诗的美妙,真的爱上了诗,是因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两字一幅画,一句一悲歌,直叫人孤孤寂寂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进而明白了诗不是供人背的,是给人吟的,让人诵的,诗不吟诵出不来味道。而我背诗坏了嗓子,又不善京韵,也不能如郭达那样用陕语秦腔朗诵《将进酒》,更无乐团来伴,李杜诗东坡词打我嘴里出来都是“沙沙”声响。因其然,腹读诗词歌赋,成了我之必然。于是乎,以为默默读,要比大声诵和轻轻吟更美。
默读的好处,可唤醒灵魂,与诗家碰撞,生出的火花,才是自家心得。
刘禹锡在陋室里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依他说来,诗不在长短,有佳句而生妙趣。句不怕短,有声色而传千古。“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蓑烟雨任平生”“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直挂云帆济沧海”,爱诗之人,定不会不为此类诗句叫绝。全诗未必记得,诗家或许不知,而这些点睛之笔直抵心田,没齿难忘。诗仙诗圣诗千万,宋词元曲万千,信手拈来者有几?《唐诗三百首》脱口百首者或不在多数。《春晓》《锄禾》《咏柳》《望岳》《花下独酌》《春夜喜雨》《题西林壁》《望庐山瀑布》,这些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诗词在诗河词海里浪花飞溅,涟漪生风,并不鲜见。
台湾作家余光中,乃世界文坛健将,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和散文,而广为流传的是他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土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每每读来,潸然泪下。我喜欢余先生的诗和散文,但一字不落记得的,只有《乡愁》。
默默读诗,也读诗人。人说“愤怒出诗人”,也觉得好诗人多被埋在寂寞里,如陆游。听听他的心声:“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如此一颗寂寞的心,不寄于诗,能与谁诉!
而我又不爱读牢骚诗。前天,昨天,今天,一肚子苦水,吐不尽,倒不完,把自己弄成了唠叨婆娘,能咋地?怀才不遇,不如李白;苦大仇深,不如岳飞;遭遇冷落,不及“三苏”,何故叫苦不迭。倒不如来几首涤荡胸襟的五律七绝,不辜负平仄对仗,悦人悦己,岂不美哉。
论道惯看之物,成诗于众所周知之事,明摆着的道理,你视而不见,我全然不知,他以诗论之,且入木三分,令人景仰。如《题西林壁》,谁不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然而,走出庐山外,辗转看庐山,论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苏轼有谁!又如“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无声处听惊雷”“春江水暖鸭先知”“病树前头万木春”,过目难忘,给人以茅塞顿开之感。
歌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诗也是。我爱阳春白雪,如爱下里巴人。虽不善平仄,拙于绝律,略知对仗,却十分地爱诗,尤其喜欢心田透亮有声色动静的诗。比如杜牧的《清明》,读来身心瑟瑟,恨不得几步奔了杏花村去,来几角酒,暖暖筋骨。
私下里,我也偷偷作过一些诗,偷偷读,不敢示人,只觉得似“诗”而非。唯“蜻蜓点水非本意,错把影花作芦花”两句,似乎是诗。因此加入了诗词协会。走进一个组织,就走近了一群人。“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走近一个专业群体,就走进了一个把日子过成诗的人群,将会遇见多少好诗好友呢。